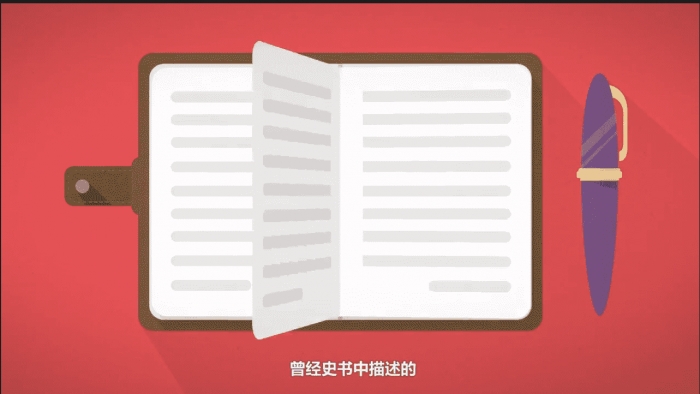从话剧到电影的非自我完善电影是一种现代化的综合艺术,按照常规它在时间的把握上、道具的筹备上、光、电、声的综合搭配上,都应当比话剧更具操作上的灵活性和方便性。但孙道临却很轻率地将《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删去了。其实,曹禺对《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是相当重视的,但是历来的导演们,从来不注重曹禺的感觉,致使《雷雨》的序幕和尾声几乎没有被搬上过舞台,这使曹禺非常失望:“《雷雨》被斫去了序曲和尾声,无头无尾,直挺挺一段躯干摆在人们面前。”曹禺、万方1985年将《日出》改编为电影剧本时,首先就“增加了序幕”,也增加了尾声——“光明的尾巴”曹禺在此所最想运用的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这部弥撒曲包括四部五个乐章,一共27个乐段,其音域广泛、结构复杂、技巧繁复、意蕴丰富,可以说是整个宗教音乐中最有代表意义的华章,具有浓重的宗教气氛,而且它包含了全宇宙中所有的事件经历、全人类所有的情感,当然也是想概括或者代表周朴园一生及其一家人的遭遇。《b小调弥撒曲》出现在“序幕”和“尾声”中对全剧具有一种预告、总结、照应和涵盖作用。它的旋律自然、朴素、优美,在教堂演唱时,具有庄严肃穆的色彩;人们听后可消除尘世俗念,体会上帝的神圣与慈爱。因此,在“序幕”和“尾声”中,以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为主,另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且与之相协调的弥撒合唱声,由音乐起,以音乐终,使全剧具有浓郁的肃穆的氛围,观众被深深地吸引到剧情中去了孙道临改编、导演的《雷雨》开幕时比较简单、直接,画面上首先出现的是江南水乡,一艘轮船穿过江桥,劈波斩浪向前挺进,这可能是告诉观众周朴园从无锡来到北方某城市;音乐也是比较单调的管弦乐的交替或并行演奏,其旋律和节奏相对简洁,如此效果,曹禺观看电影后能不表示遗憾吗?经过10年“文革”以后,曹禺的性格几乎变得圆滑起来,有时简直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如果他对电影《雷雨》没有很大的反感情绪,他一般情况下肯定是要说话的,但他却什么也未表示。这些不太重视音乐的导演们从一开始就割裂了曹禺对《雷雨》的整体思维,日式动画进化道路的一小步,割裂了文学和音乐之间那种微妙而神奇的联系,使其感染力大大削弱其次,曹禺还想让序幕和尾声给观众以“所谓的欣赏的距离。这样,看戏的人们可以处在适中的地位来看戏,而不至于使情感或者理解受了惊吓。”孙道临导演的电影《雷雨》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没有给观众一个预设的心理;到结束时,舞台上风声、雨声、叫声、哭声、枪声此伏彼起,一疯、一傻、一逃、三死悲惨欲绝,丢下一个痛苦的周朴园。观众对故事青节的变化感到目不暇接,给人的感觉是紧张激烈,扣人心弦,让观众一刻也得不到休息与放松,使观众看了以后心里很累。这样,从根本上违背了曹禺的本意。众所周知,必将造成民族的自我泯灭,“电影改编贵在创造,但终究不过是一种二度刨作。与一般创作相比,其自由度就少得多,要受到许多限制。”。改编者“要懂得原著的长处在哪里,影视视频制作不足在哪里,不要把原著的缺点扩张了,也不要把原著的精华损伤了……方是忠于原著的最好态度。”上海芭蕾舞团将《雷雨》改编为大型芭蕾舞剧,曹禺不但对改编以后的几个重要人物的性格的表现给予了首肯,同时,“曹禺对舞剧《雷雨》的音乐、舞美设计也很赞赏”。两年之后曹禺却没有给孙道临改编、导演的同名电影《雷雨》以一个字的说法,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在《雷雨》电影中,鲁侍萍似乎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敢于斗争的无产阶级女性形象:她与周朴园狭路相逢在周公馆,但她却显得非常主动、镇静,两次主动要借机溜走,离开周公馆,公司宣传片拍摄而周朴园却是主动、及时叫她留下。孙道临所要表现的是鲁侍萍要走,周朴园要留;但在话剧剧本中曹禺所要表现的正好相反:鲁侍萍要留,周朴园要赶:周朴园:(看她不走)你不知道这间房子底下人不准随便进来么? 鲁侍萍:(看着他)不知道,老爷周朴园:你是新来的下人? 鲁侍萍:不是的,我找我的女儿来的周朴园:你的女儿? 鲁侍萍:四凤是我的女儿周朴园:那你走错屋子了鲁侍萍:哦。——老爷没事了? 周朴园:(指窗)窗户谁叫打开的? 鲁侍萍:哦。(很自然地走到窗前,慢慢地走向中门) 周朴园在感觉到鲁侍萍的关窗户动作非常熟悉的时候,问:“你贵姓?”“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周朴园问鲁侍萍:“你在无锡是什么时候?” 周朴园说:“无锡是个好地方。” 周朴园一直在亲自打听或派人打听鲁侍萍的下落周朴园想把鲁侍萍的坟墓修一修的对话这样,删除了周朴园和鲁侍萍相逢时温情脉脉的对话回忆,那么剩下来的就全部是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资本家与下层妇女的辩论与争吵了。孙道临这样的改编的后果就是将曹禺原著中的周朴园和鲁侍萍等人的厚重感和真实感全部失去了。单从这一点讲,曹禺就不会同意的作为《雷雨》原著本身的意义,我觉得主要是在揭示周朴园这个封建性资本家族的毁灭。悲剧主角周朴园的悲剧性在于,它力图以其信奉的伦理纲纪维系下去的这个“金玉其外”的体面家族,无法摆脱它“败絮其中”的内在矛盾,仅仅延续到其第二代就彻底腐朽而自行溃败了——它以周萍自杀为标志,可说是“二世而亡”。周朴园对被他赶走的前妻“亡灵”的忏悔与悼念,作为一种涅赫留道夫式的“道德自我完善”,可能不全是虚伪的;也许,也正是这种忏悔与悼念成为一种呼唤,最终招致这个“亡灵”的家人及其自身重新来到他的面前,进而把他及其整个周氏家族一同带向了另一个世界。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而致使药碗摔得粉碎,可以说是这个家族的全部封建的资本的伦理关系从根底动摇的先兆;全剧死的死、疯的疯的悲惨结局,则是其全线崩溃、走向死亡的完成电影《雷雨》我看了两遍,总感到这部严谨地按戏剧“三一律”、全部依据巧合结构成的舞台剧,搬上银幕作为一部电影来看,暑假必选四款主流网络高清播放器横评,就显出了其结构上的更加明显的人为做作的痕迹。这是从艺术上讲。从思想上讲,原本代表旧中国劳资两大阶级的鲁、周两家人的势不两立的阶级对抗,一经沾上性爱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这两种关系本身又是冲突的),就统统软化了,淡化了。这可以从鲁妈特别是鲁大海身上见出,例如他对周萍与四凤爱情关系的态度的转化。当然,鲁大海只是个自发反抗的工人形象,是个很有偏见、心地很狭隘的人物,很真实,但写得不成功,他那前后两种态度至少是不讨人喜欢全片的悲剧结局或矛盾冲突的完成,也更主要借助于血缘的、性爱的,影视视频制作甚至是生物性的(如乱伦)、自然性的(如雷雨)、物理性的(如电击)诸条件来解决。这都是原著原本的致命弱点。当然它因此成为一出奇特的“佳构剧”,又有着悲剧艺术结构技巧上的绝妙的长处。这就是说,在上述种种偶然性关系中,曹禺终究还是找到了一种可谓必然性关系的悲剧冲突,这一悲剧冲突的焦点就集中在“周二世”的周萍身上:一方面,周萍同非生母之母繁漪的乱伦(这里由于对方为非生母,所以其“乱伦”还未像俄狄浦斯那样是到了可诉诸“蒸淫”罪名的极致)使他与生父不可调和,然而他对于其生父却原属同一个阶级意识与利益的继承者与被继承者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他同女仆四凤之恋,即使可以跨越两个对抗阶级的关系,却又决不可能跨越同一个生母遗传的血缘关系——这就使周萍的命运陷入了真正悲剧性的两难的绝境,惟有死路一条,方可平和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