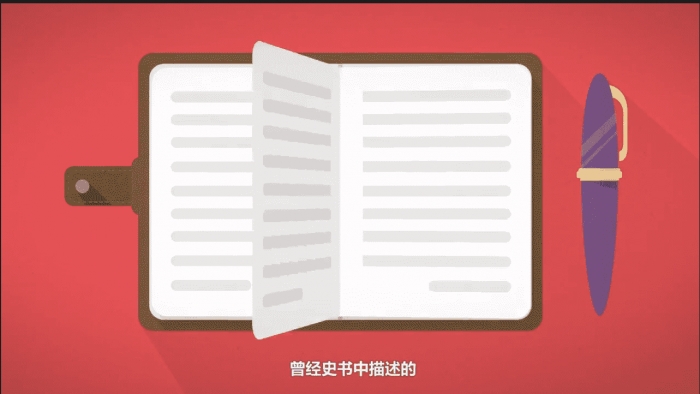用影像定格心象 转初见杨延康,一身宽松棉料衣裳,脖子上挂一串佛珠,脸上一直挂着安静微笑,剃了光头,身形高大的他说话轻言细语,谈话时他很注意别人的观点,既不乐意别人打断自己的谈话,也不会打断别人的发言。杨延康成为摄影师之前,他当过10年的安顺织袜厂的机修工人。30岁时,他来到深圳闯荡,成了一名厨师。“1984年12月31日,那个日子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两天前,我从老家安顺跟随一辆装满厨具的大卡车颠簸两天到了深圳,在一家酒店准备做面点师傅。1个月后他便辞职离开了酒店,到桂园路13号《现代摄影》杂志社做发行员,在这里开启了他对摄影的爱好。 “李媚大姐是我最重要的一位摄影的老师。我没有受过摄影训练,没有读过摄影的专修学校,只是在一个杂志社做一个发行人员。但当我看到大量的摄影来稿,还有每期杂志上主编李媚所表述出来的摄影思想,让我获益非浅。”杨延康说。《现代摄影》是当时国内比较先锋的摄影杂志,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王宁德、韩磊、包括后来的杨延康……从这里走出了很多优秀的摄影师。后来经李媚的介绍,杨延康认识了陕西摄影名家侯登科、胡武功、石宝琇,每年他有20天的创作假和20天的探亲假,他利用这40天假期前往西北去学习。之后,杨延康为了摄影主动放弃了“铁饭碗”。在杨延康的照片公布之前,许多人“谈麻色变”。在杨延康的镜头下,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麻风病人有多么痛苦,而是像常人一样的日常生活,他们也会遛鸟,也会捕鱼,也能上学读书。杨延康带着一种人文关怀,从平视甚至仰视的角度去观察麻风病人的生活,而他的照片也打动了世人。杨延康说,摄影人在拍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拍自己,只有遇到那些能够触动自己心灵的画面时,才会按下镜头。 “在中国乡村,特别是高原贫困的藏民居住区,民众虽然物质贫乏,但是精神富足。乡村民众注重心灵的追求,对生活更执有感恩的心态。”杨延康介绍,自己的镜头看向乡村,就是想把中国乡村民众纯朴、感恩以及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传达于世人。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投入藏传佛教的拍摄。采访中,影视视频制作杨延康反复提到“信仰”二字,他认为,信仰就是“灵魂的引导,它是高于艺术之上的”。正如他的自述:“我用磕长头般的信念去忠诚于影像艺术,用信仰之绳平静地系上一个心结,真正明白摄影的价值和意义。近日,其最新画册《心象》出版,作品“千中选一”,为这十年来的81幅诚意之作。他以游客的身份“闯入”藏区,但他没有游客的猎奇心理,而是潜心学习藏族礼仪,融入藏民的生活。久而久之,央视电视剧频道副总监黄海涛被带走调查,当杨延康只身穿行于西部多省的藏区时,他也成了“当地人”。10年间,杨延康每年会有8个月的时间深入到乡村之中,体验生活,沉淀自己。Focusky动画演示大师 v3,他说:“我起初也被藏地风光、民俗所吸引,拍了一些赛马、雪山,藏族服饰,后来一些念头冒出来:脱掉这些服饰,藏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怎样去度过信仰生活?什么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我尝试和他们相处,发现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触碰藏人真实而坚忍的内心。” 十年藏地摄影,杨延康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回到原乡,回到自己最初的状态,浮躁的城市呆久了,企业宣传片制作他就想逃离,只有在藏地,旅游 与松江来一场浪漫约会吧他才感觉自己是安宁的。在西藏,杨延康让一切随缘,在这个寺庙住一阵子,认识一位喇嘛,然后让这位喇嘛带着去认识下一站寺庙的下一位喇嘛,公司宣传片拍摄跟着进藏的运输车跑到下一个驿站,走一路拍一路,“影像特别饱满的时刻,就是最打动我的时刻。”他说。《心象》的封面,是杨延康2005年在青海拍摄的作品《站立山顶的僧人》。片中的主角“弱巴”是青海的僧人,现在成为了杨延康的“小兄弟”。杨延康回忆当时的拍摄过程,他说:“2005年某日清晨,我和弱巴相约去丹斗寺朝圣,拄着木杖,我们走了7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当到达山顶的那一刻,弱巴一手拄杖,一手摆动挥舞,面前是蜿蜒的黄河和巍峨的群山,站在身后的我,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于是咔嚓一下,按动快门。” 著名策展人顾铮评价杨延康的《心象》系列,是当代西藏摄影中无可置疑的优秀作品。他说:“《心象》系列作为一部纪实摄影作品,它对于藏民生活的描述,往往坐实了我们的西藏想象的某些部分,真切再现了有关藏地风光与藏民生活。但是,人物和肖像的完美摄影技巧,我们也从他的这些照片发现,他的摄影并不只是再现,同时也在超越现实的具体性而达成某种精神性方面作努力。